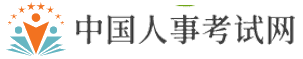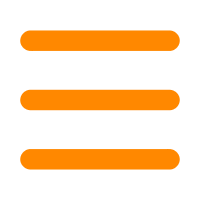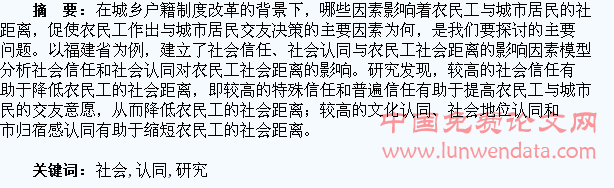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C931.7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13
1、问题的提出
自1958年开始,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化进步、稳定城市秩序、保障城市供给、控制城市规模,在城乡之间实行严格的迁徙和流动限制有什么区别化户籍规范。这一规范的形成对中国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的飞速发展发挥了要紧有哪些用途。然而,伴随国内市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转变,城乡二元户籍规范出现了很多不合理性,日益割裂着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愈加多的外来农民工遭到文化排斥、歧视、偏见与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不公、城市生活本钱高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融入。这在一定量上妨碍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在此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原因,具备要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农民工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原因,大家可以从现有些文献中找到两种主要的答案:其一是社会资本差异、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的影响[2];其二是阶层群体固有差异与社会距离有哪些用途机制[3],其中包含地理空间分布差异、文化差异、种族差异和经济地位差异。前者强调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彼此的社会融合。后者强调社会阶级环境差异化(如经济收入不平等等)致使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社会距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觉得,社会距离还与年龄、婚姻情况、个人的成长环境与家庭子女数目有着密切联系。尽管已有些研究也涉及到社会认可(如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研究。但鲜有学者从社会信赖和社会认可这个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事实上,社会信赖是缩短大家社会距离的有效工具。假如农民工有较高的社会信赖,既对自己具备影响所处的邻里社区环境的市民生活有信心(常见信赖),也对家人和朋友对我们的诉求作出反应有信心(特殊信赖),他们可能对缩短其自己的社会距离就有较高的期许。而从社会认可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以从农民工对其自己的角色定位来探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壁垒。毕竟,作为外来的、试图融入城市既有群体或者文化的农民工而言,怎么样归属和认可我们的城市角色,拉近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是对某一城市特定社会形态的认可,更是对处于这个特定城市社会形态中群体和市民的认可。认可的结果总是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偏好[4],进而影响彼此的交友决策及其社会距离。基于此,本文将探讨社会信赖与社会认可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信赖
在社会学范围,社会距离被用于衡量大家之间情感的亲密程度和关系的紧密程度,它事实上也是人与人交往间心理距离的一种反映。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不同大小的社会距离或者说是心理距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个体没办法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将来环境中准确地预测和监督别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风险。这类“不确定性和风险又是人类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因此,在缺少直接或者完全控制别人行动的客观复杂环境中,信赖变得格外要紧。信赖的大小直接预示着信赖双方关系的亲近或者亲密程度,假如将信赖的同心圆扩展到更为抽象的社会客体中,所打造的信赖,大家称为“社会信赖”。
社会信赖是指公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双方相互信赖的程度,是社会资本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6],或者说是彼此对他们能作出符合规范行为的持续性期望[7]221。社会学学者将社会信赖划分为常见信赖(generalized trust)和特殊信赖(particularized trust)?芍帧F毡樾湃问侵父鎏宥允忻裆缁帷⑻逯坪湍吧?人的一种信赖[8];这种信赖表明了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于双方之间的持续的相互认同和讲解的期望程度。特殊信赖是指对家人或者朋友的信赖[9];这种信赖表明了家人和朋友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个体认同和同意的期望。较低的常见信赖一般表现为对社会的冷漠,他们觉得除去我们的家人,其他的人或者事物都不可信,都非常现实。社会信赖较低者总是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不愿和人交流,由于他们害怕被欺诈。社会信赖较高者总是表现出对人和事物较高的依靠,且倾向于彼此的互惠。因此,社会信赖能有效促进民众之间的交流并形成某种较为公正的意识和增进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福利[10]。
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少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个体的社会距离或者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社会信赖是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紧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社会信赖与社会距离之间具备密切的有关关系。假如说社会信赖是一种人与人交往间的情感润滑液的话,那样通过交往而衍生出来的社会距离就能得到有效的缩小。“社会距离可以划分为主观个体社会距离、客观个体社会距离、主观社会距离与客观社会距离。主观个体距离可以看作个人对别人的怎么看、偏见,客观个体距离指的是个人之间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差距、主观社会距离表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看法和怎么看,这是群体之间观念差异的来源、客观社会距离反映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在整体文化、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距离有哪些用途原因包含了个体本身的主客观认识差异和个体与社会其他事物之间的主客观差距,即个体对整个社会的人和物的认识差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而这种内在屏障则表现为个体的关系、交往和感情冷淡[11]。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觉得较高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减少社会距离,当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有效缩小社会距离。因此,社会距离被用于刻画人与人在社会中关系情感的紧密程度,这其实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资本强弱的一种反映[12]。而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紧组成部分的社会信赖,自然也能被用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已有些一部分研究已经证实,信赖能够帮助调动个体行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提升个体与别人交往的频率[13],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信赖是要紧的,被信赖也是非常重要的”[7]213-238。换言之,当个体接收到别人的信赖时总是会提升自己在其他事物中的可信性。因此,社会信赖可以勉励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扩大个体的社会互联网、互动的范围、促进彼此交流、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同意等,从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的一部分。但现在较少学者具体从社会信赖的角度考察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唯一的例外就是胡荣和王晓2012年的研究[2]。他们的研究中将信赖、互联网关系与社团参与作为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的原因。他们发现较高的信赖能够帮助减少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讨常见信赖和特殊信赖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综上文献之检视,大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常见信赖能够帮助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的常见信赖越高,其社会距离也越小。
假设2:特殊信赖能够帮助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的特殊信赖越高,其社会距离也越小。
(二)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认可
在心理学范围,认可是一个同时发生“求同”和“存异”的过程。认可是一股很独特而强大的力量,虽然它是一种无形的想象,但它本身是可以建构出来的。当大家的认可存在差异时,社会的形态也会产生差异[14]。建构主义者觉得,认可是个体或者群体在肯定环境因素下,对自己身份的选择和界定,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15]。“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认可是由社会认可和自我认可所构成的连续统一。自我认可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地方的感知。社会认可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一同认可,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与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备的某些一同性和相似特点。”更进一步地说,社会认可就是“大家依据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特定阶层产生的归属感”。这种阶层归属感是阶级差异所引起的,而阶级差异既是客?^存在的,也是主观拥有些,故大家之间各自内化自己身份的归属感也在某个时期是主客观并存的。因此,这种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直接引起了个体或者群体的社会认可差异。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社会认可,导致了不同阶级之间的观念和认知等鸿沟和差异现象。而这种认知差异或者鸿沟便演化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西方学者将这种群体间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的差异与客观的文化、教育和地位之间的悬殊差距称为社会距离。因此,社会认可与社会距离是密切有关的,假如说社会认可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属阶层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法等的认同和一定的话,那样社会距离便是个体理性分类后对自己归宿身份感的要紧表现。当个体和群体对自己群内偏好和群外偏见的认可感越强烈时,群体之间为了维持各自认可的“优越感”或者消除“自卑感”而努力与其他群体维持一段距离。这事实上在无形中为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设置了妨碍[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要维持一个长期的“敌对”状况,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距离。根据常见怀疑主义学者的看法而言,当个体处于某个固定环境中时,他(她)不会千篇一律地同意,他(她)会通过比较与不断地怀疑、计算和谋划来获得新的社会认可,塑造新的社会身份。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并非固定不变的。同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更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有较高的认可或者对自己城市人身份的归属感越强烈时,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总是较高,社会距离也越小。亦或是农民工对我们的城市地位有较高的认可时,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向总是较高,社会距离就越小。
就中国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主要产生于国家规范和国家传统文化两大体系。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以户籍规范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治社会规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屏蔽”规范,它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地方划分体系中将生产资料、收入、市场地位、职业、政治权力、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社会声望等分层对待和分层处置。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权利,也看上去有失公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妨碍着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等级层次的社会,任何事都讲究级别顺序,如饭桌礼仪、会议发言等都遵循严格的先后顺利,它在中国人的社会日常起着尤为重要有哪些用途。这种等级层次现象非常大程度上就是指社会分层现象。在社会学范围,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团体因占有资源的差异而产生的社会群体地位之分的现象。它事实上潜在地反映出不同层级人群由于文化、社会地位和主观心理偏见的不同而导致人与人之间观念和认知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异所衍生出来的分层认可。不同层级的人和群领会自觉将自己归类,以提高我们的“本体性安全”。当然,这种自我归类的过程会遭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某个个体从一个熟知的环境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时,个体为了保护我们的“本体性安全”,会努力重塑我们的行为规范以期与周围环境所规定的社会规范相协调。这一过程就是个体“去个性化”和“去旧群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个体“去环境重压”的过程。因此,个领会在新环境中好好学习新的文化规范,采取各种方案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最后重新获得我们的社会认可感和被认可感。这具体表现为对所处环境文化的认可,对自己地位的认可与对自己归宿感的认可,而这类认可便导致了今天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见,农民工社会认可是农民工社会距离产生的要紧原因,但现在学界极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农民工社会认可对于其社会距离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就是1995年李强和2011年王桂新和武俊奎在其研究中有所涉及,他们觉得外来农民工在心理上有意识地维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与同群共通的偏见和价值将会扩大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等,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将社会认可作为主要测量指标,且没细化社会认可的测量指标,这不利于深入剖析农民工社会认可对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此,本项研究将在农民工的社会认可背景下,探讨其社会距离这一问题。依据对上述文献之综合,大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认可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关,即社会认可感越强,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反之,社会距离就越大。
3、有关数据统计和变量测量的办法